雪州養豬業面臨生存危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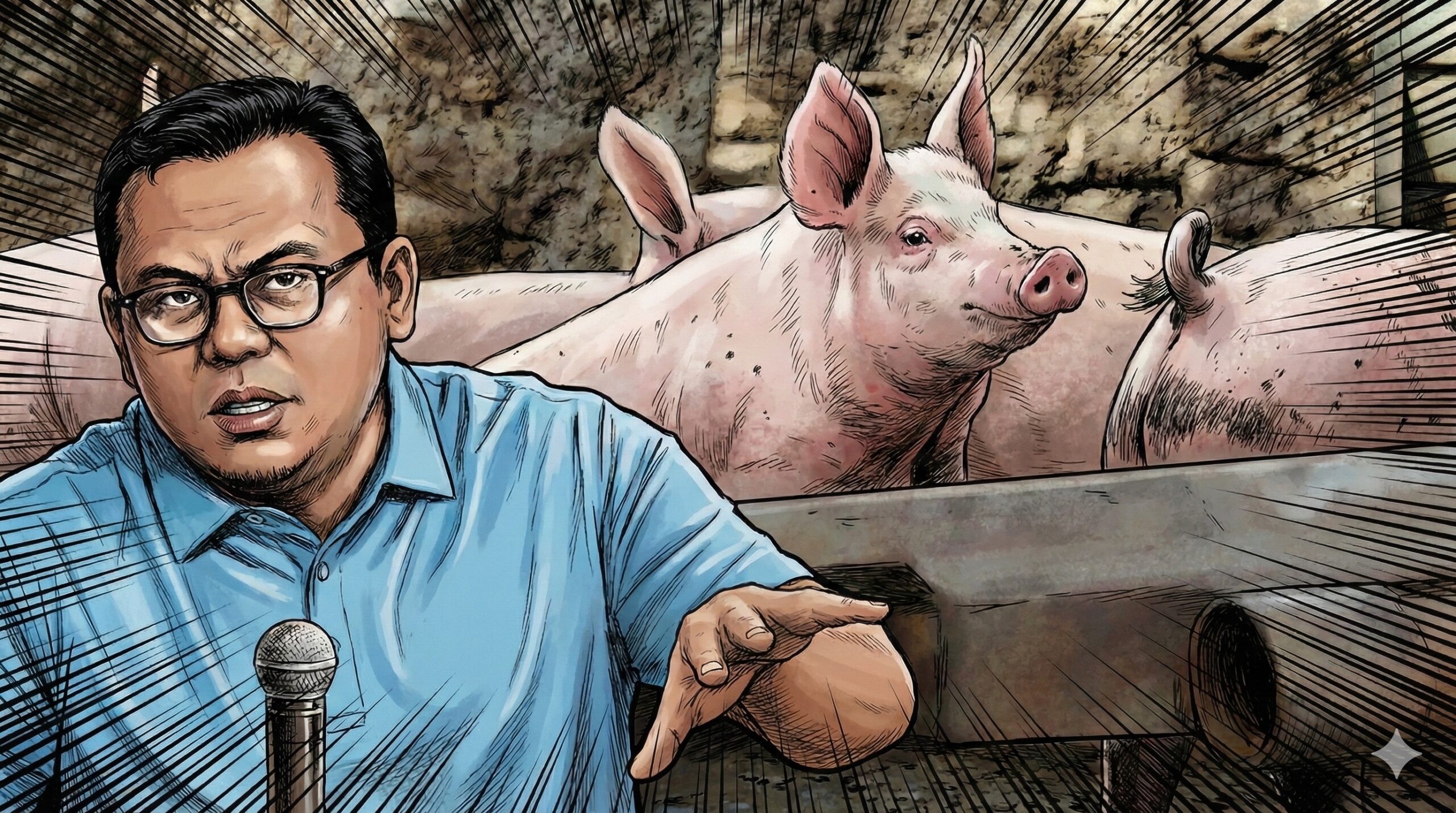
今天我們來講「養豬場搬遷」的新聞。雪蘭莪蘇丹的一道御令,直接炸開了長期以來隱藏在社會底層的結構性的矛盾,這是一場涉及王權、行政權、糧食主權以及多元社會共存底線的深度博弈。今天,就帶大家深入拆解這場發生在2026年1月的「雪州養豬業大地震」,看看在王權與民生、宗教與經濟之間,我們到底正在失去什麼。
首先,我們必須回溯到這幾天的核心事件。2026年1月10號與12號,雪蘭莪蘇丹殿下連續發表了極為強硬的御令。這道御令的核心只有一個:推翻州政府原本設定的「2030年緩衝期」計劃。大家要知道,原本在州政府的規劃下,位於丹絨士拔(Tanjung Sepat)的養豬農友們還有四年的時間進行現代化轉型或逐步遷移,這原本是一個緩衝,是一個給產業喘息的空間。但蘇丹殿下明確表示「極度失望」且「不同意」。殿下下令,丹絨士拔的所有養豬活動必須立即開始逐步停止,並且在極短的時間內完全遷移至武吉達卡Bukit Tagar。
為什麼蘇丹會在這個時間點如此強硬地介入?殿下給出的理由非常直接:第一,瓜拉冷岳地區的人口結構以穆斯林為主;第二,當地的養豬場長期產生的臭味與蒼蠅問題,已經嚴重困擾了附近的住民,甚至波及到了蘇丹的行宮。在王室的角度看來,在這種敏感地帶保留大規模養豬業,是對當地文化與宗教的一種「不敏感」。
但康哥要在這裡跟大家探討一個更深層的法理問題。在我們這種君主立憲的制度下,王室的御令往往具備強大的政治象徵意義。當蘇丹直接點名批評行政體系的決定時,民選政府的行政自主權還剩下多少?原本由專業官員與民選代表擬定的2030年轉型藍圖,在一夕之間化為泡影。這種「政策U-turn」,對投資者、對那些已經投入大筆資金進行初步現代化改造的農民來說,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。這不僅僅是養豬業的問題,這反映出馬來西亞在面對敏感產業時,政策的穩定性是何等脆弱。
我們接著來看這道御令中的「三不原則」:不準出口、不準大規模擴張、必須解決污染。這三個標籤一貼上去,基本上就是給雪州的養豬業判了半個死刑。不準出口,意味著這個產業被鎖死在內需市場,無法規模化;不準擴張,意味著它失去了成長的動力。當一個產業被限制在「只能勉強生存」的框架下,誰還願意投入數千萬令吉去搞技術研發?

大家有去巴剎的都知道,現在一條燒豬最便宜都要2千塊馬幣了,每公斤 的生豬價格從2021年的RM 8塊錢漲到今年的每公斤接近RM18塊。那為什麼本地豬肉這麼貴呢?除了飼料依賴進口之外,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非洲豬瘟帶來的毀滅性打擊。從2021年到2025年,大馬的豬肉自給率從93.4%一路崩跌到不到70%。政府過去幾年一直在喊「現代化養豬場」,說要轉型成封閉式系統,但是根據預算,要蓋一個符合標準的現代化豬場,每一頭母豬的轉型成本高達RM30,000。對於那些在丹絨士拔經營了幾代人的中小型農戶來說,這不是轉型,這是逼他們破產,逼他們關門啊。
現在,蘇丹下令要把他們搬到150公里遠的武吉達卡。武吉達卡是什麼地方?那是原本規劃的中央集中養豬區。聽起來很理想。但現實是,基礎設施至今還沒完善,高昂的遷入成本與陌生的環境,對已經在非洲豬瘟中傷痕累累的豬農來說,無疑是雪上加霜。如果這批本地豬農最終選擇放棄,馬來西亞的非穆斯林社會將面臨一個巨大的風險:我們的豬肉供應將完全掌握在巴西、美國或泰國的大財團手中。一旦國際物流出問題,或者匯率崩潰,我們連吃一口新鮮豬肉的權利都會喪失。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「糧食主權」的流失。
說到這裡,我們不能不談談這場危機背後的政治盤算。在這次風波中,馬華扮演了批評者角色。他們抓住了非洲豬瘟賠償金不到位等問題對州政府發起猛攻。說白了,馬華是想藉由農民累積的怨氣,把養豬場風波變成削弱行動黨華社支持率的議題。但在我看來,如果馬華真心想救這門產業,我更期待看到他們能拿出幾份實質的、具備法律依據的政策書,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媒體上的「口水仗」。因為在農民面臨危機的邊緣,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,比起單純的「打嘴砲」來得更有格局,也更能贏得尊重。
然而,這也帶出了一個讓選民最心寒的質問:我們選出來的代議士,在州政府中擁有龐大議席數量的行動黨議員到底在哪裡呢?我們看到,在現實的行政體系內部,面對官僚,以及來自王權直接干預的巨大壓力,行動黨議員的處境顯得極其尷尬而且卑微。
這就是馬來西亞政治最無奈的斷層:他們在立法層面 看似人多勢眾、聲勢浩大,但在執行與實質的行政決定權上,只要一碰到宗教敏感與王室紅線,往往就顯得束手無策。這種有票無權,有權又無能為力的政治困局,才是選民們最失望的無奈。
這也反映了馬來西亞政治的一個悲哀:一個經濟議題一旦被貼上宗教或種族的標籤,理性的經濟分析就會讓位給情感的政治正確。當官員在考慮要不要給豬農發准證時,他們考慮的不是國家的糧食安全,而是這張准證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仕途,會不會被政敵拿來炒作成「出賣信仰」。
那麼,難道就沒有共存的可能嗎?蘇丹提到的污染問題、臭味問題,確實是存在多年的產業矛盾。豬農們也必須承認,傳統的露天養殖模式在現代社會、在人口稠密的地區,確實已經走到了盡頭。但問題在於「轉型的方式」。
既然州政府說要轉型、要現代化,那豬農民去向銀行貸款不就行了嗎?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,但在現實的商業操作中,這簡估計是天方夜譚。大家要明白,在商業銀行的眼中,現在的養豬業簡直是「高風險」的代名詞。一場非洲豬瘟,幾千頭豬說撲殺就撲殺,資產瞬間歸零。在這種隨時可能血本無歸的預期下,哪家銀行敢開門做你的生意?
更何況,大馬豬農正面臨一個極其荒謬的「投資悖論」。大家去看,雪州乃至全馬絕大多數的豬場,腳下踩的不是自己的永久地契,而是所謂的「臨時地契」。這就是土地使用權的死結:這種地契通常每年都要更新一次,意味著農民對這塊土地根本沒有長期保障。你試想一下,州政府一邊要求農民投入幾百萬、甚至上千萬令吉去蓋「現代化封閉式豬場」,但另一邊,政府卻連一個長期的土地租約都不願意給。這就是我說的悖論:你要求我投入天文數字的資金進行永久性設施升級,卻讓我待在一塊隨時可能被收回的土地上。沒有地契作為抵押,銀行根本不批貸款;沒有長期穩定的租約,農民只能依賴自有資金或私人借貸。在商言商,你會出錢去做這樣的投資嗎?
如果政府真的有心要保住這個產業,就不應該只是發布一道搬遷令,然後讓農民自生自滅。真正的「軟著陸」應該是由政府出面,與金融機構對接,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「現代化轉型專項貸款」;是由州政府與王室達成共識,在武吉達卡建立一個真正的、具備國際標準的產業園區,並提供長期的稅務減免。
然而,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各方都在「甩鍋」。州政府說這是王室的御令,我們必須遵守;聯邦政府說養豬是州政府的權限;豬農則是在絕望中等待最後的期限。這種分裂的行政體系,正在一點一滴地耗盡馬來西亞的產業競爭力。
我們再從憲政的角度多聊幾句。馬來西亞是一個奉行議會民主制的國家。雖然我們尊重王室作為宗教與文化的守護者,但在具體的經濟與產業政策上,行政機關應該保有其獨立性與專業性。如果每一項涉及敏感性的經濟政策都需要王室點頭,或者王室可以隨時推翻既定的行政規劃,那麼我們的政府規劃還有什麼公信力可言?這對於國家的法治建設與行政效率來說,是一個需要我們深思的警號。
回頭看這幾年的社會氛圍,從禁賭、禁酒到現在的養豬業生存危機,這背後其實都有一條清晰的主線:就是在保守主義抬頭的背景下,世俗生活的空間正在被不斷壓縮。我們談論豬肉,不只是在談論一種食物,而是在談論一個多元社會的基本權利。如果一個傳承了百年的合法產業,在面對發展與宗教敏感時,只能被動地接受「被消失」或「被放逐」的命運,那麼下一個受影響的產業會是誰?
今天的這番話,可能有些沉重,但我認為我們必須面對真相。養豬業的危機,是大馬多元社會脆弱性的一個縮影。它考驗著我們如何應對糧食安全的挑戰,考驗著我們如何平衡王權與行政權,更考驗著我們這個社會對於「包容」這兩個字的真實底線。
馬來西亞的未來,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。本地的豬農需要的不僅僅是同情,更是理性的政策支持與法理的保障。希望這支影片能引發大家的思考,我們不能等到超市架上只剩下昂貴的進口凍肉時,才回過頭來後悔我們今天失去的糧食主權。